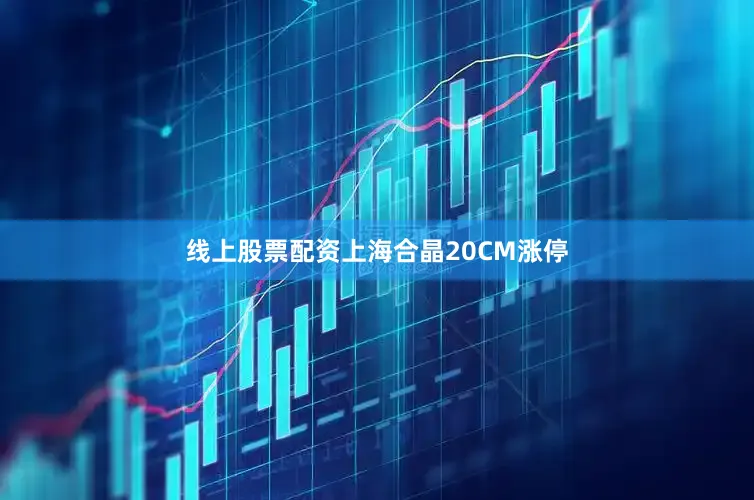那是一张如刀刻斧凿般的脸庞,挂满冰晶的眉弓下,眸光如淬火的利刃,穿透时空凝视前方,将侵略者的野心碾碎在黑土地上……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厅内,一尊名为《追随》的雕塑,将风雪与热血定格,让每一位驻足者都感受到心灵的震颤。
这尊雕塑的主人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北国雄狮”——赵尚志。
雕塑无言,可走近它,仿佛能听到隆隆的炮火轰鸣——那是赵尚志巧布兵阵痛击敌寇的智慧回响;能听见胸腔里的心跳如鼓——那是赵尚志两次被开除党籍,却始终追随党的赤子之音;更能听见穿越时空的誓言在回荡——“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那是坚定的信仰力量,让赵尚志在短暂的生命里无数次作出大我、无我的抉择,义无反顾,向死而生。
“争自由,誓抗战”
2004年的一天,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颤抖的指尖抚过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激动地呼喊:“前排中间拿马鞭的小个子就是赵尚志,‘小李先生’!”那一刻,泪水模糊了老人的双眼,却让70余年前的烽火记忆愈发清晰。
展开剩余86%这张穿越枪林弹雨留存下来的照片,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赵尚志将军生前的照片。它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那段锋锷历史、血色春秋。
1932年6月,硝烟正浓,刚组建不久的巴彦抗日游击队迎来了一位新的参谋长——这位化名“李育才”的24岁青年,因为长了一张娃娃脸,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小李先生”。人们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日后会成为名震四海的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战士们只觉得“小李先生”与众不同:虽然身材不高大,却总能在战场上智取巧攻、出奇制胜;稚嫩的面容下,蕴藏着运筹帷幄的从容与克敌制胜的自信。
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的一个贫苦家庭,年少时便目睹了列强的铁蹄踏破山河,救国救民的种子早在心底生根。1925年,年仅17岁的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便将党的使命视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同年,受党派遣,赵尚志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军事教育的熔炉中得到锤炼。
每一名“追光者”,心中都有一片要照亮的地方。离开黄埔军校后,赵尚志毅然回到家乡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暗夜寻光,危险重重。他曾两次被捕入狱,但镣铐锁不住信仰,酷刑摧不毁傲骨,任凭敌人百般摧残,他始终未吐露半句党的秘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沦陷。怀着国仇家恨,赵尚志奉中共满洲省委之命来到巴彦抗日游击队。
雪很冷,血很烫。队伍初创,环境艰苦,冬天里甚至没有御寒的衣物,但赵尚志的胸膛里跳动着比太阳更炙热的信仰。他和战士们穿梭于林海雪原,双脚冻伤、溃烂仍坚持作战,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一次次出奇制胜。
1932年8月30日,拂晓,枪声骤起。游击队联合其他反日武装兵分三路,攻下日伪统治的巴彦县城。胜利后,赵尚志和游击队的骨干们拍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居中的赵尚志比身旁的战友矮半头,但这具身躯里,却矗立着令侵略者战栗的巍峨灵魂。
命运却在此时设下严酷考验:1933年,巴彦抗日游击队遭日伪重兵围剿,加之内部成员复杂,队伍被击溃解散。中共满洲省委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赵尚志,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籍失去了,抗日的枪不能放下。这位英勇的战士,始终铭记着党把自己派往抗日战场的最初使命:痛击日寇,收复山河!
一个25岁的青年,当时他的心潮是否像黑龙江的波涛般汹涌难平?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党的忠诚从未改变,一腔报国的热血丝毫未凉。
“开不开除,是组织的事;干不干革命,是个人的事!”赵尚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追随党。他加入另一支反日义勇军部队,从马夫干起,冲锋在抗击日寇的第一线。
正如北国红松,越是风雪交加,越要挺直脊梁——这便是赵尚志,用一生诠释着何为“追随”的真正战士。
“几点委屈何妨碍卫国志士”
夏日的尚志市乌吉密乡三股流村外,细雨初霁,“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遗址”纪念碑在晨雾中肃立,碑身浸润着历史的圣洁光晕。一队武警战士肃立祭奠,英雄的气息如山林间永不息止的长风,掠过碑铭,拂过战士们刚毅的眉骨,将铁血精魂植入每寸肌理。
1933年10月10日,正是在这片黑土地上,赵尚志率领12名勇士竖起抗日旗帜。他们面对苍山宣誓:“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撞碎云霭,在群峰间荡起久久回响,将民族的血性刻进历史的年轮。
这是一支英勇无畏的抗日劲旅,赵尚志正是队伍的灵魂。他是攻坚战的行家,宾州城战役,他慧心巧思,制木炮、轰城墙,威震敌胆;他是突围战的高手,三岔河之战,他指挥若定、待时而动,带领队伍冲出重兵封锁的包围圈;他是游击战的专家,肖田地大捷,他用兵如神、先机制敌,一招“回马枪”把敌人杀得鬼哭狼嚎、军心尽散,日军指挥部直呼:“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放胆白山驱日寇,忍悲黑水灭夷蛮。”在极寒极险的环境中,赵尚志以军事家的超凡智慧整合当地抗日力量,纵横松嫩平原。密林中的游击战如漫天星火,烧得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那句“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成了日寇无奈的敬畏之词。
战斗恰似一块试金石,让真金在烈火中愈发闪亮。1935年1月,根据赵尚志的突出表现和多次恳求,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决定,恢复赵尚志的党籍,并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从松花江边到黑龙江畔,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纵横数千里,作战百余场,威名赫赫、战功卓著。冰趟子战斗、龙门伏击战……这支部队取得了一次次令人叹服的胜利,痛击敌人的同时,也如一团熊熊烈火,将军民的抗日热情点燃。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赵尚志沉重的一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为了巩固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调集数万日伪军对东北抗联疯狂“围剿”。同年年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派赵尚志赴苏联尝试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出乎预料的是,赵尚志刚一过边境,就被苏方关押起来审查。
1940年年初,赵尚志意外地接到一份中共北满省委发布的文件——《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比风雪更凛冽的,不是日寇的枪炮,而是失去了组织。但赵尚志就像游子,不管身在何方,永远记得家的方向。
命运没有把赵尚志击倒,他再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追随。在写给中共北满省委的请求书中,他字字泣血:“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遭受什么挫折,信仰之旗都永不褪色。尽管请求没有得到中共北满省委的同意,但赵尚志依然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白山黑水间。那副他亲手撰写的楹联——“几点委屈何妨碍卫国志士,瞬时落寞岂影响保家男儿”,与其说是笔墨文字,不如说是一片丹心。
两次失去党籍,却从未失去信仰;当名字被历史尘埃暂时覆盖,他用血肉之躯篆刻忠诚。漫天风雪中,赵尚志以生命作答:何为共产党员?——是星火,纵坠寒夜,必燃山河;是劲松,历经霜雪,愈挺苍穹。
“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清明时节,雨丝轻落,鹤北林业局尚志林场笼罩在薄雾中,“赵尚志将军遇难地”纪念碑前已摆满雪白的杜鹃与金黄的秋菊。从三江平原到松嫩腹地,人们携着晨露赶来,静默的祭拜里,有白发老兵颤抖的军礼,有孩童捧来的山野花束——岁月在此刻折叠,让1942年的风雪与2025年的春阳在碑铭上交融。
丰碑无言,却镌刻着人民最质朴的尊崇。那个倒在抗日疆场上的身影,终究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可他用34载生命点燃的信仰之光,早已化作恒星,在历史的天空中永恒闪耀。
再度被开除党籍的岁月里,赵尚志始终像磁针朝向北极星般追随党的方向。他对战友说出了那句铁血誓言:“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彼时,霜雪覆额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句肺腑之言竟成生命谶语。
1942年2月12日的寒夜,朔风如刀切割着梧桐河谷。在特务的诱骗下,赵尚志率领部队奔袭伪警察分驻所,却在途中遭特务从背后暗算。子弹穿透腹部的瞬间,他踉跄着转身,用尽最后力气扣动扳机,将特务击毙。
埋伏的敌人将包围圈收紧,赵尚志在昏迷中被俘。敌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这位身负重伤的将军仍怒目圆睁,血沫从嘴角溢出:“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
8小时的审讯,8小时的铁骨铮铮。当晨曦初现,松花江尚未解冻,赵尚志3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日军割下他的头颅送往长春请功,躯体则被抛入冰窟,融入刺骨的江流中。那具浸透热血的身躯,如一座凝固的山峰,将最后一滴血融入黑土地的褶皱,在冰与火的淬炼中,铸就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
198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决定重逾千钧——“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铅字,犹如满是岁月重量的砝码,决定中的“赵尚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将军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今的哈尔滨,尚志大街上车水马龙,千万次被呼唤的街名里,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密码;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把赵尚志将军曾用过的手枪似乎仍蓄势待发,金属冷光里凝固着“忠诚”二字的千钧重量。
赵尚志的英雄气概早已渗入黑土地的血脉,成为后人面对风浪时最坚实的精神根基。
追光者终将与光同辉。且让我们以赵尚志将军蘸着硝烟写就的词为祭:“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这激昂的词句穿越了80余载风雪,此刻正化作碑前纷飞的纸蝶,载着后人的追思,飞向他毕生守护的山河。
发布于:北京市卓信宝-配资炒股开户官网-配资股票网-在线配资软件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